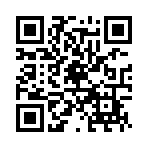在創新中探索中國電影的未來 從發祥地到成熟體系
原標題:在創新中,探索中國電影的未來
“這里有好電影、好食物、好朋友,我真心建議全世界的電影人,把上海國際電影節排入每年必不可缺的行程!”6月上海,光影交錯,為這座城市披上了最美的風景,戛納電影節藝術總監蒂埃里·弗雷茂忍不住這樣感慨。
蒂埃里·弗雷茂是上海國際電影節的老朋友了。去年,當他來到上海時,還在驚訝,剛在戛納披金奪銀的《小偷家族》《何以為家》等新片,轉身竟又在上海相遇。今年再至,他已熟門熟路得就像“回到了家一樣”,“這里的影迷很熱情,觀影文化的氛圍也非常熱烈,還能遇見很多熟悉的影人。幾周前,我剛在戛納見到《南方車站的聚會》劇組的朋友,馬上又在上海相見,感覺我們就是一個大家庭。”
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增設“戛納零時差”單元,《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最美的年華》《痛苦與榮耀》《魯貝之燈》《悲慘世界》等多部剛在今年戛納電影節展映參賽的新片“零時差”在上海亮相。我們有理由期待,在這之中,通過電影節放映的“先聲奪人”和后續的綠色引進通道,有可能誕生下一部在中國市場大受歡迎的《何以為家》。更令人期待的是,由中國電影人創造、獨具中國文化特色的影片從這里走向更大的市場和更多的觀眾。
如果說,電影產業如同一條河,從創意到制片再到發行放映走近觀眾,每個環節緊緊相扣,才能讓這條河奔流不息。在上海國際電影節,眾多中外電影史上的佳片重新匯入觀眾視野,串起了電影長河的“前史”,那么,這條河的今天和未來,掌握在新一代創作者和觀眾手中。中國電影人和觀眾熟悉歐洲三大電影節的光環,也曾頻頻為奧斯卡小金人傾倒,在中國由電影大國邁向電影強國的今天,在中國電影長河中占據重要位置的上海,正扮演電影產業鏈中的“節點”,電影節正是集聚發散資源的一個集中平臺。在這里,歸來與出發,交鋒與共鳴,中國電影這條“大河”轟鳴向前,深幽入心。
從璞玉到鉆石
“第一,你準備在哪里拍?第二,你的拍攝周期是多少?第三,你未來市場是面向哪一塊的?只有把這些問題想清楚了,你才能對預算和回報有一個全面的把握。”在電影項目創投“青年電影計劃”公開陳述現場,評委沈暘向入圍計劃的《幸福里99》導演藍天一連拋出三個問題。
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項目創投誕生于2007年,“投”出了一大批后來被觀眾熟知的作品。《鋼的琴》《白日焰火》《Hello!樹先生》《陌生》《十二公民》《師父》等一大批“電影創投項目”入圍影片,或在國際影展摘得大獎,或進入市場口碑不俗。12年來,電影項目創投見證了64個項目進入制作。就在今年電影節開幕前夕,去年入圍“電影項目創投”的兩部影片《再見,少年》《熱湯》宣布殺青,電影海報上的“SIFF Project”彰顯著它們出自“上海國際電影節”的身份。
歐洲三大電影節將知名導演攬入麾下是其慣例,很多導演身上有著深刻的“戛納”“柏林”或“威尼斯”印記——電影節是他們步入業界獲得聲譽的起點,當他們成為大師之后,也總是愿意將自己的新片第一時間送到出發之地——所謂“嫡系”就是如此形成的。相比歐洲三大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是年輕的,但從誕生之日開始,它的追求也是鮮明的。在金爵獎主競賽單元之外,2004年創辦第二個競賽單元——亞洲新人獎單元扶持亞洲新人新作,隨后又以“電影項目創投”形式為華語新人步入業界提供幫助,目前已形成創投訓練營、青年電影計劃、電影項目創投、合拍片項目、制作中項目等五個活動板塊,針對不同階段的項目,提供各環節需要的孵化、融資、推介的對接服務。通過階梯式孵化產業人才的系列計劃,上海國際電影節正在培養起自己的創作者序列。且看今年電影節,不少成熟電影人歸來并為更新一代創作者助力,就是這個序列的彰顯與循環。
比如今年創投單元評委之一沈暘,曾任上海國際電影節業務副總監,正是亞洲新人獎、中國電影項目創投、合拍片項目洽談、國際電影論壇、國際學生短片大賽等板塊的創辦者。2014年,她監制刁亦男導演作品《白日焰火》獲柏林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及最佳男主角銀熊獎,此后又監制了《少女哪吒》《東北偏北》《路邊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冥王星時刻》等一系列文藝片,堪稱“金牌推手”。今年,沈暘與刁亦男再度聯手制作《南方車站的聚會》,劇組成員在電影節開幕紅毯上的熱舞成為焦點。
又如創投單元的另一位評委、來自中國臺灣的“80后”導演陳正道,他執導的《記憶大師》《催眠大師》《重返17歲》等片在兩岸取得不俗業績。2008年,陳正道第一次來到上海國際電影節創投單元,27歲的他憑借《世界上最后一場雨》獲選“最具創意項目”。陳正道回憶,盡管創意并未很快轉化為大銀幕作品,但這次“初試啼聲”,為他找到了進入業界的一把“鑰匙”。2010年,他又帶著《幸福額度》來到上海,找到了投資合作方。第二年,影片公映,陳正道也就此邁入了電影工業的“快車道”。
再如寧浩——無須用更多語言介紹這位以“瘋狂”系列在中國電影市場攪起風暴的導演。2005年,還是新人的寧浩以《綠草地》在上海獲得當屆亞洲新人獎最受歡迎影片。14年過去,已成為中國導演中堅力量的寧浩以亞新獎評委會主席的身份回到這個平臺,發掘下一個“寧浩”。
一位業內人士評價,有影響力的國際電影節必有其藝術追求和引領,通過電影節創投和評獎將新人一步步由“璞玉”磨成“鉆石”,則是一個電影節最大的財富。“柏林、戛納、威尼斯都有自己的‘嫡系’,我們也許不這樣稱,但通過上海國際電影節平臺推出的電影人,我們將一直視為好朋友,為他們的未來發展持續提供支持和幫助。”上海國際影視節中心主任傅文霞說。
從發祥地到成熟體系
“在上海,你會留下些什么,也能帶走些什么,這座城市永遠不會讓人失望。”一位作家曾這樣說。每年電影節的銀幕上,匯聚世間最多悲歡離合,你在影院一定也會留下些什么,帶走些什么。蒂埃里·弗雷茂想帶走的是4K修復版《海上花》,來上海之前,他就把這部影片放進了自己的觀影片單里。“修復效果非常驚艷,我看到了現代技術與中國傳統之美的兼容。”看完影片,弗雷茂當即向上海國際電影節發出邀請,希望能把修復版《海上花》帶到法國展映,“侯孝賢導演曾經帶著這部作品來過戛納,所以我們也很期待它能‘回家’”。
對《海上花》來說,直面上海觀眾,是一次真正的“回家”。“《海上花》是我21年前的片子,當時要求演員們講上海話,是為了造成一種距離感,甚至于距離的美感。當時哪里想得到有一天這部片子竟然會在上海放映。你們看就知道了,原作是蘇州話,電影里講著舊的、新的、南腔北調、臨時硬學的上海話。這是《海上花》在上海放映的獨特意義吧。”侯孝賢為《海上花》的“回家”特意寫來一段寄語。
上海是中國電影的發祥地,擁有中國電影史上諸多“第一”。從1896年上海徐園的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戲”開始,上海和電影便結下不解之緣。今天,上海電影觀眾所體現出的高素質、高品位,成為中國乃至世界電影人前進的動力。電影節舉辦期間,無數美麗的重逢在銀幕里外書寫著。主角是電影的制造者,也是電影的欣賞者。“傳統的電影人都在擔心網絡電影的來勢洶洶,但在互聯網電影發展蓬勃的中國,依然有許許多多年輕人選擇走進影院。我要告訴全世界的電影人,一定要有信心,因為電影院不僅存在于過去,它仍然代表著行業的未來。”弗雷茂這樣感慨。
上海國際電影節的發展與中國電影市場的發展趨勢相輔相成。每年電影節論壇上的觀點交鋒,總是直擊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當下的痛點,成為電影產業一段時間的“風向標”。“BAT會否‘革’了傳統電影公司的命?”“中國電影市場‘熱錢’涌動,讓寫故事成了流水線上的配方。”“慢一點沒什么不好,就像人的成長一樣,電影市場的成長也是自然的。”歷年電影節論壇上,有過詰問,有過吐槽,也有過溫和的勸解。在今年,“電影工業化”成為多場論壇上的關鍵詞,折射出中國由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邁進道路上最為緊迫的需求。
在這種需求的驅動下,今年電影節,設于上海展覽中心的電影市場超過16000平方米,云集313家來自國內外的展商,覆蓋影視制作、后期、發行、營銷、教育、投融資和服務等電影全產業鏈,并新增“電影人才培養主題館”“電影投融資主題館”和“長三角影視拍攝基地主題館”。不論是制片、發行、營銷等傳統環節的影視企業,還是攝影棚、影視院校等前端基礎設施,律所、銀行等過去的“業外”機構,乃至字幕制作、天氣預報、咖啡設備等關乎影視業每個末梢的服務環節,都能在這里找到相關機構的身影。甲骨易譯制影視事業部的田發嫄告訴記者,過去,他們承擔外國影片的中文字幕譯配業務較多;近幾年,中國影視劇“走出去”的數量上升了,尤其是“一帶一路”國家小語種需求越來越多。
世界電影不僅有好萊塢一種模式,在中國,在上海,越來越多姿多彩的電影版圖正在展開。曾經,第一部中國與塞爾維亞合拍片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一帶一路”電影周揚帆,第一部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合拍片、第一個中國與烏克蘭合作的電影項目都從上海發端。今年,第一部中國與希臘合拍片在電影節期間“官宣”;來自俄羅斯、意大利等國的優秀電影合拍項目在電影市場內進行推介,“聚焦伊朗”“聚焦泰國”……無不折射著上海的視野與眼光。
“沒帶走什么,卻也帶走了很多。”6月19日,在上海返回北京的高鐵上,畢業于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電影制作專業的丁宇寫下這句感言。這位曾經的哈工大計算機專業博士生如今是一名電影制片人,上海是她學業和職場的轉折點、新起點。帶著電影項目《大好》重回上海,影片得到創投單元評委主席王家衛的大力褒賞,上科大—南加大制片人班也拋來特別關注的橄欖枝。
電影長河,生生不息。無數人在上海開啟夢境與未來。
[來源:解放日報 編輯:格若]